和其他非小细胞肺癌不同,肺肉瘤样癌(PSC)是一种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由于手术难度大,晚期PSC常常被漏诊或误诊为其他类型的NSCLC,患者对放化疗敏感度低,治疗需求难以满足[1]。近年来,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和PSC分子病理学研究的探索,间质上皮细胞转化因子(MET)酪氨酸激酶(TKI)抑制剂有望为PSC的治疗困境带来突破[2]。本文将从PSC的临床特征、诊断难点和治疗现状切入,结合近期临床研究结果进行讨论,以期为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困境——肺肉瘤样癌,一种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的非小细胞肺癌
肺肉瘤样癌(PSC)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罕见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发病率占肺癌总发病率的0.1%-0.5%[1]。根据2015年版世界卫生组织(WHO)肺部肿瘤分类,PSC可分为多形性癌、梭形细胞癌、巨细胞癌、癌肉瘤和肺母细胞瘤五种亚型[3]。其中多形性癌是PSC最常见的亚型,是一类含有至少10%梭形细胞和(或)巨细胞成分的低分化非小细胞癌(图 1)[3-4]。

图 1. 多形性梭形细胞癌 HE 染色
PSC多见于老年、男性、吸烟的晚期患者,患者平均年龄为65-75岁[1]。2020年一项纳入SEER数据库共1640名PSC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显示,PSC患者男女比例约为1.4 : 1[5]。大部分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为晚期,然而在PSC中晚期患者的比例明显更高。另一项来自SEER数据的回顾性分析,1921名PSC患者中有53%(1018名)伴有远处转移性疾病(IV期)[6]。而2017年我国一项5779名肺癌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确诊时为IV期的患者占42.4%[7]。
除了临床表现,PSC患者在影像学上也表现出一些特征。计算机断层扫描(CT)显示,PSC患者的肿瘤多位于肺上叶,边缘清晰且瘤体较大,直径常大于125px,大者可达450px,常浸润胸壁和纵隔(图 2)[1,4,8]。

图 2. PSC 患者胸部 CT 影像
但是仅依靠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PSC的误诊率很高,肿瘤组织病理学检查对PSC的鉴别诊断十分重要。然而,由于PSC的高异质性,小活检或细胞学样本无法为诊断提供充分的依据[3]。并且PSC患者在就诊时大多已为晚期,难以通过手术获得足够的组织样本,也可能造成漏诊或误诊为其他NSCLC。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手术前仅有11.6%患者被确诊为PSC,其余近九成患者被误诊为鳞状NSCLC或肺腺癌[9]。如何利用少量样本实现PSC的精确诊断,也是目前临床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PSC的临床诊断应综合考虑患者临床表现、影像学和手术切除组织的免疫组化检查结果,以避免漏诊和误诊。
PSC不仅仅诊断难度大,更大的困境在于治疗手段的局限。既往PSC的主要治疗方案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但由于血管侵犯程度高,PSC易发生转移和复发,平均术后复发时间仅6.8个月,患者获益十分有限[1,10]。同时,PSC对放疗敏感度低,易对多种化疗药物产生耐药,导致放疗和化疗的生存获益并不理想[11]。多项研究数据显示,晚期PSC患者接受不同化疗方案的中位PFS仅2-5个月[10,12],而中位OS也仅为4-5个月[12]。总体而言,PSC是一种恶性程度高、预后较差的NSCLC,相比其他类型的NSCLC死亡风险显著更高(HR=1.34,P<0.001)[14],患者的治疗需求远未满足。
MET14外显子跳变——PSC的转机
随着检测手段不断进步,对PSC分子特征的探索也不断深入。研究发现PSC是一种驱动基因突变频率较高的NSCLC,以EGFR、KRAS、ALK和MET基因突变较为常见,其中MET基因突变的频率为20%~31.8%,来自不同研究的数据显示东西方PSC患者中MET基因突变的比例相似[15-16]。
MET基因编码的蛋白c-MET是一种跨膜酪氨酸激酶受体,MET通路参与调节细胞的增殖、迁移和血管生成等过程。MET基因突变包括第14外显子跳读和基因扩增等,会导致MET通路的异常激活,从而驱动癌细胞的增殖、迁移,促进肿瘤发展[17]。回顾性研究显示,中国PSC患者中MET14外显子跳变的发生率为20.8%-22%[15,18]。
MET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一种小分子抑制剂,能够阻断MET通路的异常激活,从而起到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期待这类药物未来更多的研究,为PSC迎来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刘雷, 等, 中国肺癌杂志, 021(012)902-906.
[2]. Robin Guo, et al., Nat Rev Clin Oncol. 2020 Jun 8.
[3]. Travis WD, et al., J Thorac Oncol. 2015 Sep;10(9):1243-1260.
[4]. Ouziane I, et al., N Am J Med Sci, 2014, 6(7): 342-345.
[5]. Sun L, et al., Ann Thorac Surg. 2020 Apr 5. pii: S0003-4975(20)30503-8.
[6]. Yendamur i S, et al., Surgery, 2012, 152(3): 397-402.
[7]. Wang P, et al. J Thorac Dis. 2017 Jul;9(7): 1973-1979.
[8]. 周彩存, 肺部肿瘤学, 2016
[9]. Lin Y, et al., Am J Clin Oncol, 2016, 39(3): 215-222.
[10]. Vieira T, et al. Lung Cancer. 2014; 85:276–281.
[11]. Xin Li, et al. Sci Rep. 2017 Jun 21;7(1)3947.
[12]. 熊伟杰, 等.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4, 45(2)320-323.
[13]. Ung M, et al., Clin Lung Cancer,2016, 17(5): 391-397.
[14]. Steuer CE, et al. Clin Lung Cancer. 2017 May;18(3):286-292.
[15]. Liu X, et al. J Clin Oncol, 2016, 34(8): 794-802.
[16]. Cortot AB, et al., J Natl Cancer Inst, 20l7, 109(5).
[17]. 尹利梅, 等.中国肺癌杂志,2018,21(07):553-559.
[18]. Li Y, et al., Lung Cancer, 2018 Aug;122:113-119.
本文仅供医学药学专业人士阅读



.jpg-pd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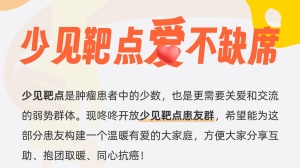
-1.png-pd13)
.jpg-pd13)
.jpg-pd13)

















 X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