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木佚在吃瓜,80后,北京大学硕士,暂时的四期癌症患者。生病前混迹于金融街,目前赋闲在家安心养病。
在社交网络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国外癌症患者的故事,无论他们是已经康复,还是正在与疾病抗争,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散发出来积极、温暖的能量。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知道正在经历什么,也知道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终点,但与坚强相伴的,是理性和豁达。
什么样的土壤能够浇灌出那样的阳光和理性?
为什么中国的患者群体,很难像他们那样,而更多的是在无助中煎熬?
经菠萝介绍,最近我与一位国外癌症康复患者Doug进行了交流,解答了我的部分疑惑。
Doug是一位三期肠癌患者(下图),康复后已回到正常的生活。他曾受益于医院的患者互助分享会,也积极参与公益组织的活动,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和帮助更多的人。可以说,专业的治疗以及群体提供的持续精神支持帮助他走过了艰难的时刻。

而不论是医院组织的患者互助组织,还是能够提供很多真实、专业信息的社会公益组织,在国内都几乎是缺失的。更不用说Doug没有提到的一个隐含的前提:最初能通过网络找到权威的疾病诊疗信息,以及和医生的充分交流、详细了解各种方案的风险和收益。
没有制度环境保障之下,我们患者或如无头苍蝇四处乱撞尝试各种偏方;或直接被“癌症”二字吓得六神无主放弃努力;而少数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患者或家属,则毅然自己开始钻研如何科学治疗,尽力向专业靠拢。更不用说还有很多患者,不分年龄老幼,都被家属隐瞒病情,从头到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缺乏正确认知、不能理解治疗的意义。
这也许解释了一部分中美两国癌症患者生存率差异。
毕竟,这是一个很多患者怀疑医院而相信大神、笃信中医排斥西医、转发的是“甩手功和郭林气功如何神奇治愈若干绝症病人”的地方。在各种患者群和贴吧论坛里药代骗子神出鬼没,经常一言不合就开撕。在网上问的问题往往简单粗暴:我得了xx病能治好么?我要是做了xx治疗能治好么?他们不知道如何在不同的选项间权衡利弊,把自己的性命押宝在网上碰巧遇见的“热心人”身上。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考虑到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才6.2%(出自中国科协调查,2015年数据),大专以上人口只占全国人口12%(出自统计局2016年4月发布的人口抽样调查公报),加上大部分癌症的老年病属性,癌症患者平均科学素质之不高,分布方差之大,让针对这个群体的科普或者公益尤为艰难。
美国能出现很多患者自发组织的公益组织,很重要的基础在于组织成员的异质性较低,他们大多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共同的信念和经历构成了群体稳固的向心力。他们曾受益于此,也愿意将爱传递下去。他们不忌惮分享自己的经历,可以妥协部分隐私,也不追求个人的回报。在这样的共同体里付出和收获可以达到一种稳态均衡,支持它慢慢发展。可以说,除了遭遇共同的疾病,他们还拥有其他足够多潜在的相似性,可以让他们成为朋友。

而我们的患者却除了疾病以外,也许再无其他共同点,他们在思维方式、处世态度、价值取向上可能千差万别。这些人可能在中国社会里本身就不会有交集,更不用说成为朋友互相帮助。此外,很多人担心歧视,不想暴露隐私,不愿让他人知晓自己患癌的事实。
可以说,缺乏相应的知识水准、没有共同的愿景、索取需求远大于付出的努力,是我们的自发性组织发展受阻的原因。
本来,处于有利地位的医院可以提高参与度,改善患者的感受。因为他们处于信息的集中点,占据专业优势,不管是科普,还是组织患者互助,都有先天的优势。
“有时治愈、时常帮助、总是安慰”是很多医生的职业座右铭,但是在医疗资源严重紧缺、医患紧张以及各种指标考核压力下,医生的手脚也被束缚住了。
——组织患者互助小组?万一突然身体出问题了怎么办?讲的内容不符合专业判断怎么办?
——集结以往康复患者的案例,做成宣传册在院内发放呢?患者不愿意公开怎么办?先答应了之后又反悔了怎么办?
——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小活页呢?门诊查房科研已经忙到死,哪来的精力再做?
医院也不是没有做宣传和患者活动,但是唱歌、舞蹈这种一次性的带有浓郁机关宣传风格的活动,与患者期盼的长效化、机制化、网络化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
可能根本的原因在于,患者更需要的那些内容很难整合到医院现有的各种考核指标里去,这样一来,自然难以实现。
看起来,我们患者注定面对的就是一条荆棘之路。
只是生活从来就不容易,但总得有一些改变慢慢发生。也许以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可以制定出更好的全民科普计划、医院能够将医生指导下的患者互助会和院内明星患者宣传纳入考核体系、有更多的专业爱心人士能够投身科普中来。
而患者本身能做的,就是努力提高知识水平,能更好的和医生合作。在普遍的共识水平提高,自己为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而不是简单的依赖他人之后,患者自发的公益组织才会慢慢生长起来,抚慰和鼓励更多的人。
毕竟,谁也不想生病后就变成一座孤岛。
期待我们自己的患者俱乐部!

本文来源:菠萝因子
本文仅供医学药学专业人士阅读



.jpg-pd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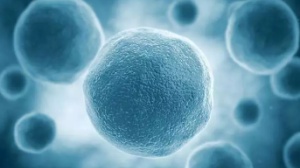

















 X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