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考了一个(注册金融分析师)一级证书。
回首这段经历,让我觉得,生病和生命中遭遇到的其他大事没什么不同,就像高考考砸了,被公司裁员了,投资失败了······都是人生不可预计之事。
在已改变的人生轨道里,找到新的乐趣和追求,是从苦痛中走出来最快的途径。
完成第一次治疗后,我带着重生的喜悦,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校园,继续为了走入金融行业而奋斗学业。
但从病痛之中走出来的我,却未曾想遭遇到了巨大的心理危机。
治疗的过程中,我把治疗结束当做坚定的目标。
可等出院,完成了这一目标,我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5 月,我顶着一个惊世骇俗的平头回到了校园。
我竭力想要回归原来的生活,回到街舞社团、像以前那样熬夜唱 K 和宵夜、与同学一起为竞争激烈的实习名额拼命、继续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
可大病之后,诸多身体的限制和夜里不断袭来的对复发的恐惧,让我失去了恣意人生的胆量,我想要赶上其他同学的步伐,却力不从心。
频密的乳腺、妇科复查和持续进行的内分泌治疗,使医院继续与我的生活深度重合。
保乳手术和腋下淋巴清扫在皮肤上留下的伤口,尽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可长长的疤痕仍清晰可见。
不敢穿无袖的衣服,也远离了泳池,我突然从一个在街舞社团蹦蹦跶跶的「疯女孩」,变成了每天宿舍、教室两点一线的「好学生」。
重疾病人可能都会经历与主流社会的分流,会经历自己可能都无法察觉的与其他价值观的缠斗;会因为自己偏离了主道而自卑自怜,甚至自暴自弃。
疾病也会以一种外力的形式,帮病人找到从「己所不欲」之事中脱离开去的借口,心安理得、冠冕堂皇。
这一次的生病,让我从一个事事都委屈自己融入集体的人,逐渐转变为一个会更加关注自己感受、对自己更为宽容和关照的人。
只是,我还未没能如此细致地思考,仅察觉到,自己已经回不到从前的生活,也融不进普通人的发展轨迹了。
这期间,我一直在竞争压力和死亡焦虑间挣扎,时而坚定,时而挫败,时而迷茫,时而恐惧。
在这种迷失慌乱的状态中,我没能躲过心里最恐惧的一块礁石:复发。
医院长长的走廊干净明亮,坐在椅子上等待就诊的人不多,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姨,我一个穿着宽大T恤和牛仔短裤的年轻人在这儿显得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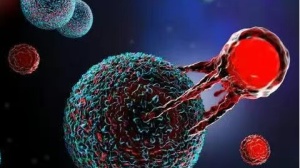





 X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