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第一次与癌症遭遇,是21岁。
2019年,我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大二,念统计专业。
作为一个理科学渣,学统计的确让我很头大,但是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课余生活给我带来的快乐,远大过了专业课给我的焦虑。
跳跳街舞、去打工 旅行、选修一些我喜欢的文科课程等、和朋友一起做一堆傻事······
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充满新奇,仿佛每个角落都在招手,向我敞开着大门。
那年6月,我想增加更多的人生体验,暑假便没有回家,在学校周边咖啡馆找了一份做店员的小时工,借住在朋友宿舍。
有天晚上,半夜三点,我躺在宿舍单人床上,无意间触碰到了自己右乳,发现皮肤表层有个硬邦邦的肿块。
那一刻,紧张随着指尖蔓延到了全身。
发现了异常,妈妈便督促我马上回国检查,我跟咖啡馆的老板说,有急事得回国一个月。
没想到,这一回,就是整整九个月。
现在回看,倘若我的人生是一张折成90度的纸,我正站在对折线上。
回到广东,爸妈带着我直奔医院。经过一些检查,当地的医生对我们说:
「去北京吧,我们这里只有全切这一条路,我要对姑娘负责。」
来不及多想,当天下午,我们全家三人匆忙收拾了几件衣服,晚上便降落在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想来,当时医生那么说,可能是「不忍心对我点破」。
到了北京某三甲医院,主治大夫看我如此年轻,马上重视起来,伸手一摸,她脸色便一沉,寥寥几句,就安排好了住院和各项检查。
八年前,医院乳腺科病房和护士站格局,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
墙上挂着的每个病房的责任护士和住在里面的病人名字,八人病房里有台要高仰着头才能看清的小电视······
记得最清楚的,是摆放在护士站旁的那一套桌椅。
坐在那张椅子上,我得到了主治大夫最终的确诊结果。
「检查结果出来了,还是直接告诉你吧。我觉得你比你妈承受能力强······你亲自跟你爸妈说吧。嗯······的确不太好,是浸润性的乳腺癌,要立马手术。」
那一瞬间,我在脸上成功地对着医生挤出了一个微笑。
不过,表面的平静,是为了掩饰内心汹涌。我迎着主治大夫关切的目光点点头,转身回到病房,呆坐了好久。
很快,主治医生安排好了由手术、六个疗程的化疗以及30天放疗组成的、为期9个月的治疗方案。
还好,没过多久,我就接受了21岁的自己患癌的事实。
没有感到过度恐慌,甚至隐约还为能休学一年什么都不干而感到兴奋。
年纪轻轻就患癌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但正是因为我还年轻,在生活和事业上「一无所有」,可能更能坦然和轻松地接受这次生命里的偶然。
当然,最焦虑的是我爸妈。
他俩当时都还未退休,只能请了长长的事假在北京照顾我。
除了医药费,在北京治病最大的花费是房租,一间小小的、简陋的一室一厅,一个月就超过5000。
当时情况发生得突然,钱上让我爸妈伤透了脑筋。
现在,我妈才告诉我,她一个从来不愿意求人的人,也不得不向别人张口借钱。
我所在是医院也有能力做保乳手术,我逃过了做全切手术的命运。
8月份做完局麻的保乳手术,又发现腋下淋巴有转移,所以,紧接着,我又做了一次全麻的腋下淋巴清扫,这让我的右臂在好几年间,一直反复肿胀疼痛。
保乳手术没有造成多大的痛苦,但腋下淋巴清扫形成的巨大创口,前后经历了3个星期左右才基本痊愈。
9月,我开始了正式的化疗。
困扰很多病友的化疗掉发,没对我造成多大负担。
在医院门诊,我见到过很多在做化疗但不舍得剃头的病友,头发特别稀少,甚至裸露出大面积的头皮,这让我坚定了开始掉发后干脆去剃个光头的想法。
某天下午,我正坐在床上看书,手指插进发丝儿间轻轻一捋,好几绺发丝就留在了指缝间。
我跳下床,对我妈说:「走,剃头去!」
带着些许兴奋和刺激,我喜提人生第一个大光头和两顶厚密的假发。
做这个决定不是我不在乎外貌,相反,是因为我太爱美了。
那时我想,与其哀叹曾经美丽逐渐消失,不如去找寻一种全新的美丽。
初到北京求医还是盛夏,不知不觉,窗外的落叶飘了下来,接着,就是白雪皑皑的冬季。
在北京完成整个治疗疗程时,已经是 2020年 2 月了。
可能说出来有人不相信,第一次患癌的九个月,于我并不难熬,甚至是一段「闲适而愉悦」的时光。
我和妈妈在放化疗期间,租了一间离医院只需步行五分钟的房子,同一小区里住的都是所谓的「老北京」,大部分都是早就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的爷爷奶奶。
每天早晨我们七点多起床,和他们一样去赶早市,在熙熙攘攘中领略着北京小摊贩的豪爽脾气。
想要快点乘风破浪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考了一个(注册金融分析师)一级证书。
回首这段经历,让我觉得,生病和生命中遭遇到的其他大事没什么不同,就像高考考砸了,被公司裁员了,投资失败了······都是人生不可预计之事。
在已改变的人生轨道里,找到新的乐趣和追求,是从苦痛中走出来最快的途径。
完成第一次治疗后,我带着重生的喜悦,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校园,继续为了走入金融行业而奋斗学业。
但从病痛之中走出来的我,却未曾想遭遇到了巨大的心理危机。
治疗的过程中,我把治疗结束当做坚定的目标。
可等出院,完成了这一目标,我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5 月,我顶着一个惊世骇俗的平头回到了校园。
我竭力想要回归原来的生活,回到街舞社团、像以前那样熬夜唱 K 和宵夜、与同学一起为竞争激烈的实习名额拼命、继续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世界······
可大病之后,诸多身体的限制和夜里不断袭来的对复发的恐惧,让我失去了恣意人生的胆量,我想要赶上其他同学的步伐,却力不从心。
频密的乳腺、妇科复查和持续进行的内分泌治疗,使医院继续与我的生活深度重合。
保乳手术和腋下淋巴清扫在皮肤上留下的伤口,尽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可长长的疤痕仍清晰可见。
不敢穿无袖的衣服,也远离了泳池,我突然从一个在街舞社团蹦蹦跶跶的「疯女孩」,变成了每天宿舍、教室两点一线的「好学生」。
重疾病人可能都会经历与主流社会的分流,会经历自己可能都无法察觉的与其他价值观的缠斗;会因为自己偏离了主道而自卑自怜,甚至自暴自弃。
疾病也会以一种外力的形式,帮病人找到从「己所不欲」之事中脱离开去的借口,心安理得、冠冕堂皇。
这一次的生病,让我从一个事事都委屈自己融入集体的人,逐渐转变为一个会更加关注自己感受、对自己更为宽容和关照的人。
只是,我还未没能如此细致地思考,仅察觉到,自己已经回不到从前的生活,也融不进普通人的发展轨迹了。
这期间,我一直在竞争压力和死亡焦虑间挣扎,时而坚定,时而挫败,时而迷茫,时而恐惧。
在这种迷失慌乱的状态中,我没能躲过心里最恐惧的一块礁石:复发。
医院长长的走廊干净明亮,坐在椅子上等待就诊的人不多,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姨,我一个穿着宽大T恤和牛仔短裤的年轻人在这儿显得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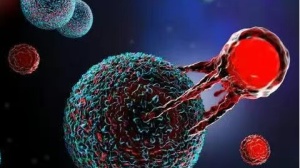





 X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