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现在是广东电视台的一名民生记者。五年前妈妈患癌时,我还在广州读大学,大二。妈妈在我心中,是个很能干、很要强的女人。但患癌经过一段时间辛苦的治疗后,妈妈有些气馁,非常悲观。在她面前有一重又一重的难关需要克服——治疗乳腺癌时是全切,化疗之后,又要面临肺部手术,那里还有肿瘤,可能是转移。
好在妈妈最终都顺利过关了,康复5年。今年身体小恙复查,并没有复发。
一
妈妈1967年出生,高中毕业后,就在贵州都匀一家棉麻纺织厂车间做流水工。后来工厂不景气,她上班也是断断续续,把我带大并不是那么容易。
妈妈的婚姻并不美满,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我和妈妈一起生活,父亲从生活中彻底消失了,没有了音信。
不过,妈妈是我心中的“女神”——她曾是个一米七的“潮女”,顶着当季最流行的卷发、穿着黑色长裙、踩着12公分的高跟鞋……带着我在老家那个小城市的大街上“耀武扬威”。
我和妈妈的关系一直相处融洽。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凌晨,我上网查答案估分,发现总分不尽人意,半夜在家嚎啕大哭。
平时妈妈对我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格,但在这次关键的高考中,她却一改往常,反而安慰我说:“没关系,大不了咱们再来一年,或者读个差一点的学校也没关系,实在不行我养你。”
后来,总分出来了,我超出重本线8分,还算不错。妈妈知道分数时立马抱着我哭了。我知道,其实我妈是个很要强的人。
二
遭遇癌症是在2015年。我在广州读大二,那年暑假我没回贵州老家,想着出去接一些主持工作,兼职赚点经验和零花钱。
7月24日下午2点半左右,我背着重重的主持服离开宿舍,刚走到一楼电话就响了,是姨妈打来的。
“你在干嘛?”
“正赶着去市区主持呢,怎么了?”
“你方便回来一趟吗?”
“不是说了好几次今年暑假不回去吗?”
“医生说她那个地方长了一个肿瘤,是恶性的。”
我顿时懵逼得说不出话来,她又补充一句:
“而且医生说已经转移到肺了。”
挂电话后,我尽量克制着情绪,默默回到宿舍收拾行李。收拾到一半,我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喂?怎么了?”还没来得及回话,瞬间泪如雨下,嚎啕大哭。妈妈边安慰我别担心,一边和我一起哭。室友给我塞了几百块,让我赶紧回去。
18个小时的车程没合眼。回来后寒暄了几句,我看了看诊断书:乳腺癌、肺转移。这六个字刺得眼睛生疼,我说了句:“没事,这小医院,有可能误诊呢”。
第二天一早,我俩直奔省城,来到了贵州最好的肿瘤医院。结果是:确诊乳腺癌、肺转移待查。
根本来不及伤感,马上办理入院手续。病房不大,加上我们一共四户人家,都是乳腺癌患者。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快70岁的婆婆,乳腺癌晚期,全身多器官转移。在弥留之际,她几乎是昏睡不起,老伴儿日夜守候着。
入院后医生建议做PET-CT,能把病灶看得一清二楚。当时贵州没有这项技术,而且费用高昂,1万元一次,非医保范畴。
亲戚凑了钱,咬咬牙,坐火车前往最近的成都。检查结果是:乳腺癌确诊,暂无转移迹象,肺部肿瘤性质依旧不明。
回贵阳后,医生的治疗方案是:马上进行一个疗程的化疗,待肿瘤稍微缩小后,做手术切除左侧乳房,不然病情恶化得很快,肺部肿瘤再做下一步打算。
妈妈对化疗的生理反应巨大,别说米饭,喝一口水都会全吐出,没东西可吐了,就干呕:“不活了”、“我死了算了”……
辛苦熬过第一次化疗后,妈妈的乐观和自信也被化没了。但越接近手术、她的情绪越发低落。有时,半夜背对我默默流泪、莫名其妙发脾气说不活了…而我的百般安慰,似乎对她的厌世情绪毫不奏效。
手术如期而至,整整6个小时,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还活着吧?麻药散去后,一整夜汗如雨下,哭着求护士给她打止痛针。
五天后,妈妈可以下地走动了,得把吃饭的解决了吧。我俩找到医院附近的菜市场,她一边和菜贩讨价还价,一边说:“你学着点啊,等我死了你不会饿死”。
打两天化疗、吐三天、休整两周,再开始下一个疗程,如此循环。几个回合下来,妈妈体重直线下滑,脸色苍白得吓人。
我每天在医院陪伴着妈妈。天黑了,病房的人都睡了,失眠君总来找我。好几个凌晨,我偷偷走出病房,坐在楼下花园里,一条条回复朋友、老师、同学的关心短信。回复完了,偶尔悄悄下次“雨”打个“雷”,平复了就回去睡觉。
在一间几乎全是癌症病人的医院待三个月是怎样的体验呢?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确诊癌症,隔三差五就有人不治离世。有一天中午,隔壁病房一个40多岁的阿姨突然瘫坐在走廊嚎啕大哭——她刚上大学的女儿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同病相怜的病友们有些不知所措,有的上前安慰,有的偷偷抹泪。
终于,化疗结束,指标正常,可以出院了。难关还在前头:肺部肿瘤的手术,定在半年后。
三
2015年2月1日,我和“女神”如期回到医院,又将是一场持久战。检查结果不是很理想,肺部的肿瘤相较半年前增大了,若确诊是恶性肿瘤,那她的生命将正式进入倒计时。这次手术更像一次选择题,若切下的肿瘤是良性的,手术顺利结束;若是恶性,切除大面积肺,但危险系数会大大提高。
早上八点,手术开始,下午一点,医生出来了:“放心吧,是良性的,她马上就能出来”。
这个结果比中了彩票头奖还值得欢欣雀跃。妈妈睁开眼后第一个问题是:“良性还是恶性?”“我都说了肯定是良性”,愣了几秒,泪如雨下。
尽管后来的三天她依旧经历了钻心的疼痛,我每天屁颠屁颠的忙着做菜、陪她聊天,三周后,康复出院。
记得那天踏上回家的火车时,她和我说:“我终于不用比你死得早了”,真是又晦气又温暖。
四
之后的两年,我在广州经历了实习、毕业、工作。在做民生记者的头两年里,我接触了很多求助类采访,其中癌症患者占绝大部分,有不幸同时患上白血病的三岁小孩和年轻爸爸,有怀孕8个月才查出患有癌症的准妈妈。
“癌”这个词,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重了。很多时候我都会鼓励他们:没事,很多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只要坚持治疗就有机会治愈。每每对受访者说类似的话,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和“女神”一起抗癌的那两年。
当我认为一切都将好起来的时候,一次复诊又出了新的麻烦——盆腔内出现一个13厘米左右的肿瘤,医生怀疑是癌细胞复发转移。
我拿着报告,奔走在广州的各大医院肿瘤科。医生说,若是癌细胞复发转移,存活率非常低,但每个医生都不敢下定论,只建议尽快手术确认肿瘤性质。
几经考量,我俩决定再次回到老家的肿瘤医院手术。这次再回来,她的心情很复杂。这是第三次签手术同意书,要整个部位全部拿掉。医生告知了手术可能出现的所有风险,还是那个熟悉的“选择题”:良性,皆大欢喜;若恶性,生活质量将会大大下降。
与13厘米肿瘤的狙击战在不知不觉中打响了。她的信心几乎为零,情绪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躁动,甚至萌发过轻生念头。“身上该有的东西都切掉了,活着还有什么用?”
她进手术室后,朝我挥了挥手。门关上的一瞬间,我眼眶模糊。和两年前一样,手术室外依旧只有我一个人。4个小时内,“死神”好像来过,因为我听到了其他家属的哭声,我甚至一度不敢望向那扇宣判命运的大门。
终于,门开了,医生将大肿瘤摘掉了:“看,这就是肿瘤,像个早产儿”。手术苏醒后,妈妈不再关心肿瘤是良是恶,反而叹了一口气:“我好像生了一个孩子”。
很幸运,“女神”再次遭遇的是良性肿瘤。
五
今年的7月28号,“女神”给我打了个电话,最近身体不太舒服,经常胸口疼、肚子疼,我说那得赶紧去复诊啊!看了看日历,惊觉距离2015年7月被确诊乳腺癌,已经过去整整5年了。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她来电话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医生说没问题,一切正常,没有复发,可以安心了。”
经历六次化疗、三次大手术的抗战,终于胜利了。
有研究显示,乳腺癌是治愈率较高的一种癌症,只要5年内不复发,基本算治愈,不出意外将能长期存活。
不知不觉,这场与恶性肿瘤长达5年的搏斗,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5年带走了不少东西,却也留下了不少东西,总的来说,我倆的努力,总算修成了正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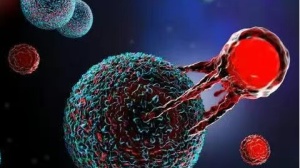





 X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