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2018年4月确诊宫颈腺癌,2019年1月复发,复发后一路治疗至八月底。
妈妈是腹膜大网膜转移,因为转移造成的小肠粘连,肠道像一节一节的麻花辫,现在下了梗阻导管,也没能解决的很好。
这十几天我一直在找“舒缓治疗”的内容,其实早在我妈确诊复发后我就在看了。只是妈妈从不参与治疗方案的制定。她是医生,这么久以来却不愿面对,惹的做下每个决定的我都很痛苦。
这八个月来,妈妈完成了六次大化,联合了阿帕替尼,可结果不理想。紧接着立马就上了K药。八月初因为疾病进展又联合了乐伐,每一次决定都觉得“这一定会对妈妈有效的,一定会有奇迹发生在妈妈身上。可上苍一次次将我们推入无尽深渊。
和大部分“赌博失败”的病友与家属一样,我后悔着过去的每一步决定,想着如果当初那样做会不会现在完全不一样。如果第三次大化后就换方案会怎么样?如果早点碰到靠谱的那位教授医生会怎么样?如果第一次手术不请上肿的医生来手术而是直接去上肿会怎么样?如果肠梗阻以后直接下小肠梗阻导管而不是做结肠造瘘会怎么样?如果妈妈没有生病……会怎么样?
可如今还是陷入了这样绝望的境地,且我知道,未来我一定会后悔此时此刻正在做的决定,面对生死,这真的是无法避免的。可能我还是会让妈妈吃卡博替尼,磨成粉混合进水里喝进去。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我也真的不敢想。有时候很羡慕生病的父母自己可以做决定的子女,因为只有“自己为自己负责”才能让疾病的治疗更有希望,我终究不是病人,无法感受到病人身体上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肿瘤病人来讲,有时候真的决定了生死。
我是一名大四在读学生,希望妈妈好。死之隶属于生命,正与出生一样。举足是在走路,正如放下足也是在走路。
癌痛,旷日持久的疼痛,尽头都不让你看到的疼痛。我感觉自己已经在慢慢接受失去了,最近一两天头脑有些空白,好像什么都没做,好像什么都没想。
回想刚确诊肠梗阻的八月底,CT上只写着“局部肠管受侵伴肠梗阻”,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面对肠梗阻。医生让下胃管保守治疗一下,我们拒绝了,两天后直接上了手术台做了结肠造口。
我那会儿还安慰我妈说“你这样便秘都没事儿,粑粑很方便就出来了”。可没想到还带着小肠梗阻......。
医生让出院了,就很直接要赶着你出院了。然后我们就又开始讨论舒缓治疗的问题。结果我妈妈自己说想去舒缓治疗且想清楚了,我说我尊重她的决定,这么久以来她终于可以为她的生命做一次主了。
擦着泪启程去上海,头一次这么这么这么不想去上海,因为这一次的上海,可能就是意味着告别,永别。
我们去帮妈妈看静安区那里的安定病房了,不知道那里究竟怎么样,如果真的很舒服很舒服,我希望即将逝去的人,和需要继续生活下去的人,都可以尽可能乐观的去面对。
我上午对我爸说,最悲伤的人不一定是我,但受影响最大的一定是我,我的人生还未正式开始,就要面临失去她了,她为我创造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虽然二十年来她和我基本没有谈过心,不像很多在家庭里劳作的妈妈给我做饭,可就是她创造了我,我的独立坚强,我的无忧无虑。现在她可能真的要离开了,我需要如此这般坚强的去面对死亡,死亡,可能真的只是走出了时间。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颗小星球,逝去的亲友就是身边的暗物质。我愿能再见你,我知我再见不到你。但你的引力仍在。我感激我们的光锥曾彼此重叠,而你永远改变了我的星轨。纵使再不能相见,你仍是我所在的星系未曾分崩离析的原因,是我宇宙之网的永恒组成。”
我已经在想今后会有多苦痛了,没有“老妈”可以叫,我生病了没有人第一时间给我联系人找人关心我,过年过节老妈再也不会拉我去陪她逛街,那个熟悉的声音再也不会唤我名字......。
痛苦绵长,往后余生我都不得不去体味。今晚八点多打了吗啡,可她醒的频率很高,都是难受醒的,她皱眉起来我就跟着难受,我希望老天爷放过这样美好的她,又希望我还能留住她。
我知道妈妈希望我好好生活下去,要像曾经一样,满怀希望和梦想,像她在时一样幸福的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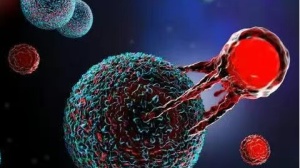





 X
X